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传播途径 |《寄生虫学研究》特刊
标题:From the wild and the tame – zoonotic parasites
微信原文:点击阅读微信原文
原文作者:Srimathy Sriskantharajah
翻译作者:Miao YU
毋庸置疑,人类难以免受灾祸/瘟疫(plague)。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双关语(译者注:plague既有“折磨、灾害”之意,也指“鼠患、瘟疫”),因为我们与家畜和野生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共享同一个生态环境。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流行,人畜共患病寄生虫的威胁日益令人担忧。事关全人类的“One Health(同一健康)”可能是控制当前和正在出现的人畜共患病的最佳方法。考虑到这一点,Domenico Otranto, Christina Strube 和 Lihua Xiao 组织了一期关于“人畜共患病寄生虫:同一健康挑战(‘Zoonotic parasites: The One Health challenge’)”的特刊。

(图片来源: pixabay)
《寄生虫学研究》(Parasitology Research)出版的特刊《人畜共患病寄生虫:同一健康挑战》提供了世界各地野生动物和家畜共患病寄生虫的最新信息。人类和动物都面临着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风险。人们可能通过与野生动物的互动——特别是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城市化——以及通过我们自身对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感染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我将回顾该特刊中的三篇综述,内容涉及人畜共患病贾第虫病、人畜共患病寄生虫分别通过肉类和野生动物的传播。

《寄生虫学研究》(Parasitology Research)
贾第虫病是由寄生在受感染的人和动物肠道内的十二指肠贾第虫引起的。它会导致严重腹泻和脱水(除其他症状外),并且贾第虫还会通过粪便被排出并传播给他人(例如,当它污染了食物或因手部不卫生而被摄入等)。在他们对人畜共患贾第虫病的综述中[1],Weilong Cai及其同事指出,对该寄生虫基因型分布的研究表明,人畜共患贾第虫病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普遍。他们说,人畜共患贾第虫病的主要根源来自一小群动物,如非人灵长类动物、马、兔子、豚鼠、栗鼠和海狸。

通过摄入受污染的肉类传播是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主要途径。例如,一些人认为COVID-19病毒是通过中间宿主的肉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在他的综述中[2],Sameh Abuseir描述了阿拉伯世界通过肉类传播的主要人畜共患病寄生虫。在该地区,肉类的主要来源是牛、绵羊、山羊和骆驼,而通过肉类传播的寄生虫分为两类:蠕虫和原生动物。带绦虫是该地区最常见的蠕虫,而牛带绦虫(牛肉绦虫)是最有可能的病因(因为其他疾病大多通过养猪或猪肉消费传播)。
同一报告还指出,弓形虫病在该地区通过食用受感染的肉类而传播。然而,家养动物体内的原生刚地弓形虫可能因国家而异。例如,在埃及,寄生虫在绵羊中的血清感染率为43.7%,山羊为64%,牛为10.8%,鸡为14-47%,骆驼为17.4%。然而,在苏丹,骆驼的血清患病率在13.3%到38%之间。来自突尼斯、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摩洛哥的报道称,这些数据(在当地)是完全不同的。
该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对肉类需求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密集的农业养殖,并导致寄生虫感染的肉类在牲畜中传播进而被人类消费的风险。在总结这份报告时,Sameh Abuseir呼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更好地“监测和控制人畜共患病的肉类传播感染”。
关于来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病威胁,Marcos Antonio Bezerra-Santos及其同事回顾了负鼠在将人畜共患病寄生虫以及病媒和媒介传播病原体直接传播给人类和家畜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3]。

负鼠原产于美洲,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的,它们看起来也很可爱),但它们也是几种重要的人类和家畜寄生虫(利什曼原虫和克氏锥虫)的宿主和病原储存库,以及立克次体等其他寄生虫的放大因子。再加上它们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在人类改造的环境中大量繁殖,因此它们在人畜共患病中的重要性也变得更加突出。
蜱是携带立克次体寄生虫的节肢动物,它们以多种动物为食,包括野生动物(如负鼠)、家畜和人类。当负鼠在野生自然区域和农业或城市区域之间移动时,与它们密切接触的动物和人类就会被侵袭,并通过蜱虫交换人畜共患寄生虫。
跳蚤是负鼠携带的另一种节肢动物疾病媒介——其中包括导致鼠疫的细菌——Bezerra Santos及其同事建议应该对负鼠作为鼠疫的潜在宿主进一步研究。
负鼠与利什曼原虫(通过沙蝇)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区的人类、狗和猫之间传播有直接联系。例如,在巴西东北部,当该地区负鼠数量增加时(在一年中较冷的雨季),人类内脏型利什曼病(又称黑热病)的新病例就会增加。
与前面讨论的肉类消费案例一样,人畜共患寄生虫可以通过食用(非法狩猎的)负鼠肉传播。克氏锥虫(可导致恰加斯病)就被认为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蠕虫等体内寄生虫亦是如此。
该报告的结论是,不仅要呼吁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这不足方面的研究仍然),还要呼吁向公众普及直接接触这些动物(例如通过猎杀它们)所带来的风险。
我不认为我们能永远摆脱人畜共患传染病——仅仅是因为我们与动物有着如此密切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且生活中同一个环境中。即使是野生动物,我们也会与它们互动,特别是当我们通过城市化侵占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人畜共患病寄生虫传播给人类的风险。这些措施包括更好的卫生习惯、更好的耕作方式、减少对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的影响、减少食物浪费(这样就不会引来野生动物到我们的垃圾箱/垃圾桶寻找食物)等等。
参考文献:
[1] Cai, W., Ryan, U., Xiao, L. et al. Zoonotic giardiasis: an update. Parasitol Res 120, 4199–4218 (2021).
[2] Abuseir, S. Meat-borne parasites in the Arab world: a review in a One Health perspective. Parasitol Res 120, 4153–4166 (2021)
[3] Bezerra-Santos, M.A., Ramos, R.A.N., Campos, A.K. et al. Didelphis spp. opossums and their parasites in the Americas: A One Health perspective. Parasitol Res 120, 4091–4111 (2021).
如果篇首注明了授权来源,任何转载需获得来源方的许可!如果篇首未特别注明出处,本文版权属于 X-MOL ( x-mol.com ), 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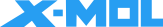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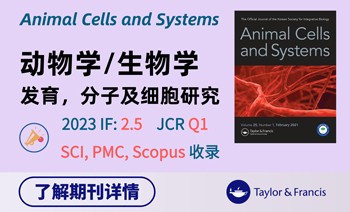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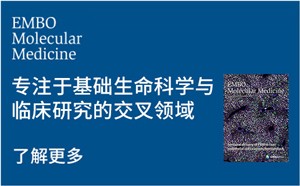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42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423号